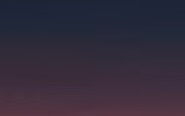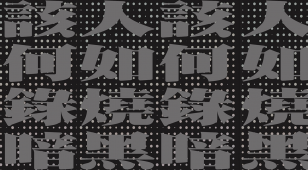此刻,在依然陌生的島嶼上

此刻,在依然陌生的島嶼上
──讀廖偉棠《劫後書》
廖偉棠《劫後書》分為三冊:以類似組詩形式呈現台灣歷史片段的〈拓孤之地〉、講疫情下日常的〈凶年巡禮〉,以及寫現世抗爭與記憶中香港的〈母語詞典〉。在〈拓孤之地〉中,詩人化為鬼眼,凝視流經島嶼的時流與血。如二戰時的神風、二二八、白色恐怖、雷震案等。然而除了島嶼歷史與政治的轉折,廖偉棠更加關注島上的詩與藝術、文化與語言的命運。如「那個寫詩的人不再寫詩/而是在庭院裡燒畫的時候/他的鄰居開始用被禁的語言寫小說」(〈1963年,紫陽花〉)。
因為語言的台灣實際上也是世界的台灣。如寫長居台灣的詩人西川滿的〈1939年,哺舌〉:「這是兩個國語,/兩個互噬的國語。」不只是世界的台灣,也是出沒於時間軸上任意位置的台灣,如來自希臘神話,又指科幻作品的「地球就是海伯利昂」(〈1942年,鳳林鬼語〉),以及流行文化的「我的哆啦A夢們/你們知道銀翼殺手與明和電機嗎?」(〈1944年,另一個時間不感症者〉),克羅齊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」在《劫後書》得到了詩意的驗證。
然而不得不問,當如此多的「你」、「我」頻繁切換於不同時空、視角、事件與經驗中,在每位詩人皆有其技術極限(口吻、修辭、意象群)的限制下,是否可能對歷史中的實際行為者有僭越、代言之虞?詩人如何避免在歷史中發言,卻僅抒個人情志?我認為廖偉棠解決此困境的方式有二。其一為在主題上,避免直接處理已被固化、符號化的關鍵事件,而從某個具體但精微的側面著手。如〈1929年,禪雨〉從連橫《台灣語典》中的台語詞彙「禪雨」寫其個人史、〈1970年,浴室裡的吶喊者〉從衛兵聽到蔣中正晚年在浴室裡的哭號,寫他和「鬣狗一般的祖國」的羈絆。波赫士曾提過一種稱為「迅捷」的詩質,即當詩人必須面對如蛇髮女妖美杜莎(Medusa)般的主題時,直視女妖絕非上策,因其眼神會令觀者立即石化。唯一的辦法是從盾牌上的反光推測女妖行動,再予以打擊。
廖偉棠在〈拓孤之地〉中的歷史書寫,正與波赫士的「迅捷」不謀而合。